長安,是漢太祖劉邦費盡心思所打造的一座偉大都城,上接西域下承巴蜀,還有渭水通關,因張良贊同婁敬的建議,劉邦始建都長安。
長安城自建都以來,一直是個交通重地,因通西域之路漫漫,而長安成為唯一通往西域的最終站點與起點,所有貨物皆在此進行貿易,因而大大促使長安城愈加繁華,進而吸引西域外邦前來,外國使節絡繹不絕,而此時的佛教禪學仍未西進。
在繁華的城都,非官者,士農工商就是所謂的百姓,百姓所勞動的區域漸漸形成所謂的市井,平民百姓故而又有市井小民之稱。
而所謂的江湖,就是由市井二字延伸而來,江湖人即為非官者而出身於市井之人。
很多人不清楚此二字的定義,秦朝前也尚未有此名詞,但這是很早就形成的一個社會形態與共識,早在春秋戰國時期,就有戰國四公子招收為數上千的門客,這是較早官方所掌握的在野門派。
比較有明確的說辭是在春秋戰國,齊國宰相管仲曾言:「士農工商四民者,國之石民也,不可使雜處,雜處則其言哤。其事亂,是故聖王之處士,必於閒燕。處農必就田墅,處工必就官府,處商必就市井。」
管仲所言的市井原意為商賈買賣的場所,但在秦末漢初天下初平,雖然劉邦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,但各處仍需大量民工聚市來加速建設,不只長樂宮復修未央宮始建,咸陽城被項羽焚燬後,亦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與物資重建,故而四民混雜相處,市井不再是商賈買賣場所的專有名詞。
第二個曾言與江湖有關的是始皇帝贏政,他曾多次遭人暗殺,而這些暗殺者皆為劍客與俠客,秦始皇二十九年,第三次巡遊至博浪沙,遭到張良尋求的力士以鐵椎砸車未果,秦始皇大怒命人追捕時說道:「奇人異士那怕藏於怒江躲至深淵,亦得掘出。」
兩年後,贏政微服出巡至蘭池宮附近又遭到一群「強盜」行俠客義行,特來刺殺贏政,最後被贏政等衛士誅滅,贏政大怒:「這些自詡行俠仗義的強盜,口口聲聲說誅朕為替天行道,可笑,殊不知這天下皆歸朕有,汝等來自三江五湖的劍客又或市井出身的小民,亦是朕之掌中物。」
最後一位為江湖定義的人,正是出身市井的無賴帝王劉邦,他可以說是最早為江湖二字定義的人,因為他本就是出自江湖的江湖人。
漢初劉邦封賞功臣,但由於大臣們相互爭功相鬥了一年多,劉邦取笑眾臣如市井潑皮,群臣不滿地向劉邦抗議,並說劉邦亦同市井出身,這話不也是拐著彎罵到自己。
劉邦聽罷倒也沒生氣,想了一下笑言:「吾等出身三江五湖各地,滅秦為行俠義之事,征戰四方為市井小民,豈是為了封王稱帝而爭權奪利?吾等有除秦滅楚之志,應當鴻圖大展,安天下為民求福祉,民非賤民,是謂江湖人,吾等皆出自江湖。」
自此,江湖二字終為定案,所謂的江湖人必行大義之事成為市井小民的美談。
簡單來說,春秋戰國四公子各擁門客逾千,這是屬於官家私有化的門派,而現今江湖之說即是拉幫結派,只是已變成民營門派罷了,這些人雖行江湖俠義事,實際卻與朝廷沒什麼兩樣。
所以這江湖與朝廷看似兩不相干,實則二者關係密不可分。
文帝元年,長安城燭火通明慶春祭,家家戶戶同賀新帝法令,大讚皇帝賢明,其實這些年,呂雉統治的漢朝,百姓也沒吃什麼苦,百姓們僅僅只是虛應一應故事罷了,當下新令一出,那能馬上看出成效。
暫且不談新帝政令大事,來講講江湖小事罷。
長安城一隅,有戶人家大院,門面雖無商賈之家的金飾門環朱紅大門般華麗,但門前那二座石獅子卻顯氣派十足,獨院佔地有千百畝,在長安城裡可稱得上大門大戶。
此戶大門上有匾額題字:「上官」。
走進上官府大門,可見廳堂與東西廂房,圍其四周空出中庭,廳堂其後為私室閨房,上官府的居所為傳統合院建築三進四合院,東西廂房給予門下劍客居住,廳堂為招待來客,中庭則為練武場。
是夜,上官府慶春祭,在東西廂大開酒席招呼同道,所謂同道,已非戰國時期的食客與門客,而是所謂的門派、世家與浪跡江湖的俠客、劍客。
上官府廳堂,席桌齊列對坐,桌上菜餚用精緻小碟子盛裝,甚至連難得一見的青瓷酒壺都能讓席上劍客人手一壺,席上眾人個個氣質不凡,身著衣飾皆為絲綢長袍,盡顯貴氣逼人。
眾人向坐主位的主人舉杯:「上官兄,這回我們可風風光光幹了件大事。這可都是沾了你的光啊!」眾人臉上欣喜之色顯露無遺。
「矣,別這麼說,鄙人無德不才那能做什麼事,這次能成大事都是諸位的功勞,該說是鄙人沾了在座各位的光。」坐在主位的上官孚謙遜回應對方,以酒回禮,眾人皆飲盡。
「嘿,打虎親兄弟,上陣父子兵,在座的各位誰不是好兄弟,說這些做啥。」眾人起哄又是各乾一杯。
「莫說這上陣父子兵,我瞧令郎那劍法使得行雲流水悠然自得,似是未盡全力,我看他應該盡得你無上劍法的精髓。」
「說起這逆子,幼時心高氣傲的模樣還挺逗人開心,但大了就驕傲自大,目空一切,唉,就算學盡天下最高乘的劍法也是無用。」
「哈哈,年輕氣盛是難免的,待得年歲稍長就會收歛許多。」
「咦。」上官孚環顧眾人:「先不提這逆子,丰老去那了?」
「丰老兒啊?他適才在這坐不住,就蹦去東廂玩樂啦。」
「那我得去與他敬個酒不可。」上官孚說畢,起身吩咐奴僕備酒。
「這老兒不過是個跑腿的,上官兄何必對他如此客氣。」席上之人見狀略有抱怨。
「哈哈,這次的大事還真多虧他來牽線,否則我也無法聯絡同道共襄盛舉啊,各位且候我一會。」上官孚向眾人拱手離去。
「哼,上官兄真是的,怎找那些只會喧囂鬧事之人前來,沒了自己的面子,貶了自家格調。」席上有人不悅,眾人無不點頭同意。
無怪席上眾人會有如此想法,這上官府的東西廂可是另一番景象。
這群自詡為俠客的大漢各自圍攏席地而坐,那邊要肉要酒的換一聲,就有奴僕送上一大盆肉與一甕酒,江湖人不大注意這小事,只要有酒有肉,還能向同道吹噓自己的本事有多大,就已足矣。
酒宴還未開始,大漢們早已開始大行酒令,這東西廂彷如市井叫賣般吵嚷,手上拿取的肉塊煮的不甚精緻,嚐起來還算美味;嘴中喝的酒,不是廳堂席上之人所喝的玉液瓊漿,而是辛辣到喉裡的白乾,眾人舉碗互乾,他們喝酒用的不是高貴的酒器,而是份量不小的大碗公,碗與碗互相撞擊酒水四溢,盡顯江湖中人的豪邁不拘。
東廂的角落中,一群大漢圍著一個老人而坐,老人身前擺著一大盆肉塊、五大甕白乾,這老人一手拿著雞腿吃得滿嘴油膩,另一手拿著只餘半碗的酒水。
「快吃快吃,吃完快講啊!莫叫人等的心急。」其中一名大漢催促著留著白鬍的老人,老人彷若沒聽到一樣,將雞腿啃得乾乾淨淨,餘下雞骨仍捨不得似的舔了又舔才丟在一旁,再一口氣狂灌僅餘半碗的酒水,這一喝完,旁邊又有人幫他倒滿一碗,老人才心滿意足道:「適才說到那?」
「就說到丰老您帶了人進入鐘室。」
「哦,對、對,太尉命人將一些兵器和鉤爪置於鐘室,老兒就領著上官門主經由地道進了鐘室。」原來這眾人稱之的丰老,就是北宮伯子曾見過的手持酒葫蘆的白頭老叟。
只見這丰老談起這事精神矍鑠,恨不得整個江湖人都知道自己參與過這件翻天大事,朝廷人稱這事為諸呂之亂,江湖人則稱季秋兵變,名稱雖不同,指的卻是同一件事。
原來這留名千古的平諸呂之亂,江湖人竟有幸參與其中。
呂雉死後沒多久,呂祿與呂產密謀改朝換代奪取劉氏江山,劉章自妻子之處得知後,隨即通知大兄齊王劉襄起兵反呂,另一方面,秦震得到劉章的消息後,以太尉周勃之名,聯絡陳平、陸賈等人策劃一場誅呂之亂的大計,其關鍵在於兵權皆在呂祿與呂產手中,如何奪得兵權?
巧婦難為無米之炊,若要說漢朝開國功臣周勃、陳平,豈非一代名將,可惜手下卻無重兵可用,這難事無人可解,就在二人煩惱之際,竟有江湖義士來投,近千眾供太尉驅使。
最終按約定好的時刻,江湖俠客入宮兵分二路,先殺呂祿奪得兵權,再引呂產入宮而殺之,爾後盡誅呂氏族人,諸呂之亂終為平定。
只是這事僅記載於鄉間野史,終不為人所知。
「精彩!精彩!」眾好漢聽畢無不拍手稱快,其實這些血氣方剛的江湖人那懂得這呂氏爭權是否為利,或是呂雉殘殺戚姬與諸王之惡,呂雉治理漢朝近十五年,廢挾書律、重儒生興書典、安撫匈奴,國泰民安,百姓豈有不知,僅僅只是民風純樸、人性本善,百姓認為天下共主本為劉氏,而今竟有外戚奪權,怎能不將其誅滅以斷其慾呢!故而拍手叫好。
「嘿,我瞧朝廷人也是有英雄風範。」
「你個鄉巴佬,前人說沒知識也要有常識,沒常識也要懂老祖先的歷史,大尉周勃與右承相陳平可都與眼前諸位一樣出身江湖,那個出身江湖的人,沒有英雄氣度?」
「說的對!」此話一出,眾人又是一番稱讚。
「真要論英雄,我瞧那劉章倒也有幾分神似先帝,殺起賊子來不輸給我們這些混江湖的。」丰老笑皺了眉頭,看起來十分滿意。
「丰老快說說,您覺得還有誰稱得上江湖英雄。」
「劉章、周勃、陳平、陸賈可稱得上。」
「別提那些入朝為官的人,我們這些近千眾江湖人難道沒有人配得上英雄二字?」
「呵呵,有、當然有,若沒我們這些俠義之士,劉章等人焉能謀定江山。」丰老摸摸那半長不短的花白鬍子想了想:「適才所說的乃是朝廷雄才,現在來談談我們這些江湖奇才。」
「別吊大家的胃口,快說啊。」
丰老清了清喉嚨,又喝乾一碗酒水才道:「老兒有些醉啦,話若有些不清不楚的,還望多多見諒,那麼就先來論首位江湖英雄非上官孚門主不可。」
「對、對!」眾大漢額手稱慶。
「上官門主不只自創無上劍劍法,令無上門不僅在長安是眾所皆知的行俠仗義大門派,在關中地區更是聲名遠播,不啻無上門是首屈一指的門派,上官門主更是英雄中的英雄。」東廂眾江湖人起哄叫好。
「至於第二位嘛,該說這行事風格亦正亦邪的邪王卜邪。」丰老話未說畢,又喝了一大口不知何時倒滿的白乾,這時卻有不少人議論紛紛,有些人不知卜邪是何人物,更有人嗤之以鼻。
「卜邪手中沾滿無數同道的血,這等人物豈可為英雄!」有人出聲駁斥丰老的意見。
「呵呵。」丰老笑了一下:「我不敢說邪王所殺之人是否皆為該死之人,至少他統合巴蜀一帶擅用蠱毒宗門的人,建立起邪盟,這不能不令老兒佩服。」
「這等人不配稱為英雄好漢,我兄弟可是死在他手裡的。」群眾中有人憤憤不平抗議。
「你兄弟是誰啊?」眾人紛紛向他問去,但他卻不說只罵道:「巴蜀一帶,卜邪惡名昭彰,就連夜哭之兒都會止啼,卜邪我呸。」
「哈哈哈哈,好個我呸。」這時卻有人放聲大笑,大家的眼神齊齊望去,狂笑之人是個頭禿肥碩的大漢,他兩手都拿著雞腿坐在地上:「卜邪之惡連夜哭的孩子都會止啼,這好啊,殊不知有人的名聲卻驚得各家有夫的美婦夜夜無法安睡。」責罵卜邪的人一聽臉色頓時一黯不再出聲,可江湖人最為好事,皆向光頭大漢詢問。
「這等醜事我本不願講,丟了我巴蜀之名,只是你的嘴太臭污衊了人,我不得不講。」光頭大漢向那人說道,那人大怒:「你!」
「你什麼你,也不打聽打聽本人是誰,居然還敢在此放肆,我可是西蜀一帶專逮惡人的亭長(捕快、警察)劉光。」
眾人一聽雖然有些訝異劉光的身份,但倒沒有很畏怯與排斥,劉光環顧眾人的表情,手拿雞腿指著適才辱罵卜邪的人道:「他兄弟叫朱劍,憑著一身好輕功常在巴蜀一帶幹些見不得人的買賣,抓不到他是我們這些亭長下卒技不如人。
這倒也罷,只是那人渣後來姦淫有夫之婦,似是食髓知味,短短一年犯下了百多件,壞了百多婦人的名聲,有的婦女受不了辱自縊身亡,若諸位自家妻妾受此辱又將如何?」劉光話還未說完,已有許多人睥睨剛才那個為他兄弟出氣的人。
「這朱劍弄得巴蜀一帶人心惶惶,那怕白天有些姿色的美婦也不敢出門。
不過終究老天有眼,在某天月黑風高之夜,他娘的這賤人又去城南一戶犯案,我們才剛趕到,他就抱著美婦飛奔城外,我們這些人拼死拼活追了出去,正想還是慢了一步追不到人,卻沒料到在路上見著了個直挺挺的人,地下還躺了個人,我們過去一看。
你們大家猜怎麼著?地下躺著的人是那被竊的婦人,而站著一動也不動的竟是我們追捕許久的朱劍。」
「他怎不動?被點了穴嚒?」有人疑問。
劉光搖頭:「死了,就這麼站著死了,只見他面無血色,一臉驚愕的模樣,彷如見著鬼一樣。」
「那這和卜邪有什麼關係?」
「是沒什麼關係,我們將屍首帶回去檢查發現,朱劍怕是真給鬼嚇破膽了,那整顆心竟然斷成兩半。」
「呵呵,怕事情不是那麼簡單吧?」丰老突然插口道。
「著啊,還是丰老有見識。」劉光向丰老比了個大姆指:「人犯就這麼死了,我們只得草草結案,總不能說是鬼神之罰罷。
數天後,我同下屬去酒樓吃酒,聽到個叫化子吹噓騙酒喝,一開始聽到他說什麼邪王為了追捕淫賊,竟大老遠從益州北上來到巴蜀尋人,最終找到了那追捕一年餘的淫賊,一掌就把他打死了!
聽到這我就感到奇了,跑去問那叫化子的,幫他叫了一罈酒一盤香炒鴨舌,他才說那淫賊叫朱劍,年前在益州淫人妻子後跑了,這朱劍人不只賤還是個腦袋有洞的傢伙,那處不犯案偏在益州犯案,邪王就住在益州,他這不是在老虎嘴邊拔毛自找死路嗎?
我後來又問叫化子怎知道,他說邪王走了自然是事情辦完了,我直罵他胡謅,要他把酒和肉還來,他反罵我怎不自己去官府問問朱劍怎麼死的,我問他朱劍怎死的,他說肯定是被邪王的誅心掌所殺,一心兩半絕無例外,聽他這麼一說我反倒傻了,這叫化子似乎沒說謊。
我後來命人去益州查探消息,果然誠如叫化子所言,後來我託人奉上大禮給邪王,豈知邪王並未回益州,據說是要來長安辦件大事,剛好我有要事來這辦,也就順便來這碰運氣了。」劉光說完,眾人大大讚揚卜邪當真英雄好漢,甚至還有人猜卜邪要來長安辦大事,莫不是季秋兵變?
「英雄英雄,天下為英雄之名所累而不自知者眾多,還沾沾自喜,英雄狗熊不過一念之間罷了。」忽有一人悠然嘆道。
「敢問貴姓大名?」丰老望向那人,那人年約四十許,一副精明幹練的模樣,理著短髮頭綁青色布帶,衣著短衣和袍褲,見那脖頸肌肉結實、豹頭猿臂,看來是個功夫不錯的練家子。
「賤名不足掛齒,就叫老子……老王。」
「王老弟,適才那句何解?」
「那還不簡單,今若呂祿贏,英雄為他,狗子為陳平等人,而丰老和近千江湖人恐怕就是個龜孫子,不得不躲起來。」眾人聽老王一說,隨即向他叫囂怒罵,什麼直娘賊、死潑皮的話都罵出聲來。
「哈哈,沒這回事,老兒不論輸贏都不會是龜孫子,老兒至始至終都是個市井無賴、老猴兒,這龜孫子……龜孫子……」丰老講著講者突然不語。
「怎?」老王疑問。
「嘿,乖啊,我這老兒居然也有個龜孫子應聲啦。」眾人一聽知道老王著了道,忍不住哄堂大笑,老王氣得站了起來,走向丰老:「你!」
「莫怒莫怒,開個玩笑,不看老猴臉面,也該瞧瞧上官門主的面子。」只見丰老身影一閃,竟然一下就蹦跳到老王身旁,同他勾肩搭背示歉,一碗酒水遞去,老王二話不說接手乾了也算是受禮了。
丰老隨腳一翻,將地上一罈酒踹了上來,另一手接著為老王倒第二碗:「莫提這事,我來講件趣事,不知有誰要捧捧老兒的場。」
大家一聽,馬上鼓掌叫好,更有的吹起口哨催促丰老。
「其實這次季秋兵變,我倒遇了件怪事。」丰老以罈就口喝了幾口:「那晚,很亂,人死很多,血跡攤在地上像條河流,屍體層層疊疊讓平地像個窟窿,著實說了,沒上過戰場的幾十人見了還都嘔了,尤其在空中飄散的血腥味,真像活在地獄裡。」眾大漢安安靜靜聽著丰老述說,有些膽子小的臉色都有些發怵。
丰老拉了拉身旁的老王一同坐下,順道再幫他倒了一碗酒:「老兒我……其實也認真想過,或許王老弟的話沒錯,英雄狗熊一念間,成者王敗者寇,那怕在江湖這道理也說得通,但這世道終究是講仁義道德,因呂氏無仁德所以失敗,或許將來劉氏無道義也會改朝換代,這天下終非一家所有,亦非有仁德者擁有,但殘暴者必亡是不變的道理。」丰老語重心長,又喝了幾大口白乾。
「話說的遠了,那晚兵分二路,上官門主率領同道先襲呂祿,而老兒是個跑腿的,欲打算先行偵查宮內埋伏的路線,正當我準備回報予朱虛侯劉章時,卻見著了個黑衣人藉著夜色在宮中奔走。
老兒心道這莫不是呂產發覺不對勁派人來查勘,不行,這人得先拿下,可是我這人腳下功夫不錯,但叫我拿人可沒那本事,所以我打算先從後跟蹤,看看這人打算做些什麼。
只見這黑衣人行去的方向既不是呂產的居所,也不是劉章的住所,他竟往宮中一處奔去,老兒也不知那是什麼宮殿,就見那人跳上屋簷,在那邊摸東摸西,摸了好一會兒,取出一樣物品,藉著月光映照下來的影子,看來像似圓形的東西,然後黑衣人用黑布包覆起來負在背後,跳下了屋簷,我心想不妙,隨手折了根樹枝當暗器丟了過去,想阻他一阻,豈料那暗器未及身前一尺,竟被他打下來,我還未來得及看清那人用何手法。」
丰老說到這裡,將右臂的袍袖掀起來給大家一看,露出一條蜿蜒曲折有如蜈蚣爬行般的傷疤,因瘡傷初癒而顯得鮮紅欲滴,遠遠一看彷如蜈蚣仍活著。
眾大漢一看個個不禁心驚膽顫。
「在那瞬間,忽然覺得右臂一疼就被傷了,我只得急忙回報劉章,也不敢再去理會。」丰老嘿了一聲,又喝了幾大口酒水,似要為自己壯壯膽。
「丰老是否有見到黑衣人長相?」有人好奇問道,丰老搖頭。
「好啦,老兒醉語,諸位英雄好漢聽聽罷了。」須臾,丰老向大家拱手示禮,眾人各自散開坐在別處,又開始聽別人講些江湖趣聞,而丰老自己則坐在原地獨自喝起酒來。
老王瞧著那如蜈蚣般的疤痕後沉默不語,待得丰老語畢,又想了片刻才道:「敢問丰老飲酒向來如此豪邁?」
「咦?沒這回事,老兒向來飲酒不過兩罈,不過近來酒量倒似愈來愈好,總覺得喉嚨癢癢兒,不能不喝。」
「丰老信我與否?」老王聽丰老這麼一說,臉色變得凝重起來。
「這是……」丰老驚覺對方臉色沉重,看似不像說謊的樣子。
「你這傷……」老王不理會丰老,擅自掀開右臂布袖仔細查看:「怕是中了酒蠱。」
「酒蠱!」丰老一驚,手中那罈酒竟落了地,幸好老王反應快將罈子接住,輕輕放置地下才道:「來。」
老王隨手拎了兩甕酒,領了丰老到中庭角落,藉著稀微的月光倒也勉強能看清對方的臉色。
「丰老見多識廣,該知道苗疆一帶有所謂的養蠱人。」丰老驚覺事態嚴重,只忙著點頭靜聽對方說話。
「這我就不多說,蠱毒種類繁多,凡蟲皆可種蠱,蠱毒變化雖多,但總跳不出那幾種,而你是被人種了酒蠱。」
「這酒蠱究竟與酒有何干?」丰老這時想起近來酒量大增,難道是與這蠱有關?
「這酒蠱該說是易解是難解,還很難說,但或許並沒有什麼多大差別。」老王邊說邊敞開短衣,露出精壯結實的肌肉,其胸前有一條暗色微凸似龍似蛇的長型紋身,老王指著這紋身道:「這是酒蠱,但與丰老不同的是,這是酒蛇蠱。」
丰老見了渾身上下感到毛毛的,雙手在兩臂抓了抓。
「當年老─咳,我中了這蠱是十多年前的事。」老王講到這,眼神顯露出憤懣:「這是賤內害的。」
「什麼!」
老王說起十多年前,妻子是苗疆一帶的養蠱人,後來因為愛上遠地而來的公子,受了那人蠱惑用酒蠱毒害自己,但天可憐見也是命不該絕,遇到年長的養蠱人所救,而這疤也就這麼擱下了。
「我這蠱似乎與你所中的不同?」丰老聽完他的遭遇,搖頭嘆氣,但神情已不如初時那般驚惶,他猜想老王既然喚自己出來,應該有法子解身上的蠱毒。
「基本上酒蠱乃是以自身血肉來伺養蠱,初時看似肉疤呈鮮紅,中蠱者會因血中精華被蠱毒所吸,而會喉嚨乾癢欲尋酒喝,酒會愈喝愈多而不自知,待蠱養大後,不是往外鑽,而是往血肉裡鑽到體內,接著自內臟開始吞咬,非得要內臟吃得一乾二淨才肯從屁洞鑽出來,屆時中蠱者還未等到內臟被吃完,就被這蠱活活折磨至死。」丰老聽完渾身一抖。
「自古眾人皆畏蠱,那是因為不了解,只要知道蠱的來由多半可以解的。」
「那少半呢?」丰老一臉半信半疑的看著老王。
「少半就是為時已晚。」老王一臉挽惜,丰老見狀整個人楞住。
「丰老莫驚,您是屬於那多半可以解的!」老王哈哈一笑。
「他奶奶的!」老王這一笑,丰老才明暸老王必定是為了報那龜孫子之仇,暗自罵了一聲。
「一人一次,互不相欠!」老王搭上丰老的肩,隨即臉上轉為慎重:「這酒蠱其實極易解,但種蠱人的手法各有不同,一不小心解蠱人和中蠱人都會同死,所以我得要再問清楚,這蠱是如何中的,中了多久?」
丰老又重新細說當晚的情節,老王點頭不語,想了好半會兒才道:「這酒蜈蚣蠱或許可解」。
老王隨即動手,先在傷疤上下一寸餘的地方用繩子綁緊,取出小刀倒了些酒在上面,才在蜈蚣狀的傷疤上淺淺地割了好長一道傷口,奇怪的是血並未從傷口流出來。
「這……」老王眉頭一皺,雙手不由然地發抖,呼吸突然加重,眼神竟有些呆滯,片刻後才回神,改在傷疤前縱向切開一寸長的傷口,這時血才自傷口處流出,老王趕緊命丰老將傷口處趴在酒罈口,讓血流在酒中,老王再開另一罈酒,以手潑往傷口處。
這一潑就潑了半罈,也沒什麼動靜,但兩人都很有耐心的等待,直到老王手中那罈酒快見底,丰老才感到手臂有些癢想去抓抓,老王急忙制止:「快成了!」
話才剛說完,丰老右臂猛然感到有種疼到骨子裡的痛,他緊咬牙根忍著。
老王繼續將餘下沒多少的酒水潑盡,此時傷口表皮竟微微蠕動,似乎有某種東西想要鑽出來一樣,從一開始緩緩的蠕動漸漸形成愈來愈大的浮動,丰老疼的冷汗直流,就這麼忍了近一柱香,丰老忽然有種蟲在皮膚表面爬行的感覺,接著一個黑漆漆的蟲子自傷口外探出頭來,兩根觸毛彷彿在揮舞一般,這蟲子似乎很有警戒心,在表皮處遊移一陣子,那觸毛掃盡傷口周圍後,似乎發現什麼,一口氣衝出來,往那酒罈爬去,沉入那裝滿白乾的酒罈,一股黑色黏液猶如黑蛇般蜿蜒地緊隨在後,直至流出來的黑液漸漸轉為白色再變成鮮紅色,這時老王才鬆口氣,將丰老扶起來止血。
「大恩不言謝。」丰老慎重向老王躬身答謝,老王趕緊將他扶起:「不須如此。」
「適才……我瞧王老弟見傷口未出血,臉色似乎有些訝異,是否有什麼異常?」
「不,只是……我剛才說過,同一種蠱毒,會因種蠱人的手法各異而有不同解法,而種蠱於你的手法卻是極為稀有,應該說是獨門手法。」
「原來如此,對了,還未問及王老弟將何去何從,是否能讓老兒做個東道─」
「丰老,門主找您!」老王還未答話,驀地,就聽到有人叫喚,兩人只得匆匆約定三日後在長安最有名的醉仙樓見,丰老隨即一躍而去。
「真是好輕功!」老王見丰老雖上了年紀,但身手依舊不凡,老王轉身望著兩罈酒,一罈已然見空:一罈滿滿的酒水卻藏著劇毒無比的蜈蚣蠱。
「王老弟!」不知為何老王竟瞧出了神,連有人來到身邊都沒注意,驚了一下轉頭一看竟是去而復返的丰老。
「其實我有句話忘了問,我們該是初逢,你也未曾參與季秋兵變,為何會救我這個一隻腳踩入棺材裡的老兒?」
「哈哈,只因為丰老曾讚我一聲英雄,如此罷了。」老王走近酒罈邊,一腳踹碎了空酒罈,而那碎瓦片餘勁未停擊碎裝滿酒水的罈子,剎時酒水飛濺,酒中那條四寸餘長的蜈蚣翻了個身正準備轉過來爬走,老王又是一踢,碎瓦片在空中裂成四段疾馳射向蜈蚣,將牠斷成五截總算死透了。
「好巧勁!」丰老見老王踢瓦片的手法有二下子,拍手稱道。
「丰老啊,您怎麼不見了,別作弄小子啦!」這時遠方傳出無奈的語氣。
「見醜,後會有期!」老王向丰老拱手告別,丰老也同他回禮,再次消失在他面前。
「長安臥虎藏龍,人人做得大事亦很豪邁。」老王望著丰老離去的方向,豪爽大笑。
另一頭,丰老總算回到東廂。
「丰老可是讓鄙人等好久啊,這不行,得先罰一碗!」上官孚取兩碗酒水,一碗遞向遲來的丰老。
「對不住,對不住,老兒這就自罰三碗。」於是連灌三大碗白乾,眾人替他叫好。
「鄙人來找丰老,是特來感謝丰老做牽線人,讓諸位英雄好漢有幸參與誅外戚滅奸臣這等俠義大事,諸位敬丰老一碗!」上官孚與眾人隨即乾了一碗。
「不敢、不敢,適逢其會罷了!」丰老謙稱,眾人聽他這麼一說皆起哄了。
「門主,丰老這適逢其會的事可多了,還在宮裡見鬼了!」人群中忽然有人說起丰老在宮中遇見黑衣人的事,瞎鬧丰老是見了鬼。
「這可不得了,傷勢可否痊癒?」上官孚眉頭一皺詢問丰老。
「呵呵,不礙事。」
「那就好……」上官孚面有難色:「只是……這宮中失竊之物不知是否貴重,又是否會令朝廷人對吾等江湖人……」
「門主這麼一說,老兒初時也深感不妥,只怕他們對吾等江湖人有些誤解。」
「只是不知那人是朝廷人亦或江湖人,丰老雖未見得面目,但是否可從身手、步法或其它地方看出端倪?」
「老兒鼻子可靈通的很,酒香味在十里外都逃不過我的妙鼻!」丰老自豪的指著自己的尖鼻,但隨即苦笑:「可我這老眼昏花又是夜朦朧,怎看的清楚。」
「難道當真無半點軌跡可尋?」上官孚的臉色略顯焦急,或許是擔心朝廷人對江湖人的態度改觀,畢竟他不同於一般江湖人,上官孚在長安立足已久,財大業大又有家累,若朝廷欲對江湖人不利,上官孚所創的無上門必定首當其衝。
「門主莫慌,其實我已秉報太尉,太尉只說那是龍口觀,觀上有四龍,龍口中有珠,那龍口觀荒廢已久,怕只是那龍珠被竊,他們會查辨的。」
「這就好。」上官孚鬆了一口氣,向眾人告辭後回到廳堂,酒席盡散已是一個時辰後的事。
豈料,隔日已過午時,上官孚仍未起床漱洗,奴僕入內去喚,竟發現上官孚橫死於內寢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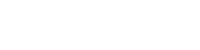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